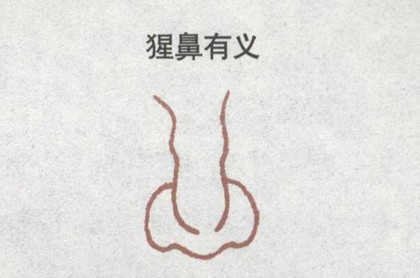【黃梅戲的特點是(shi)什么?】
在中國五(wu)大(da)戲劇里黃梅戲以(yi)抗日題(ti)材及愛情(qing)故事(shi)被人(ren)(ren)們所喜(xi)愛,在黃梅戲文化中許多名人(ren)(ren)對它也(ye)是(shi)(shi)諸多好(hao)評。那么同學們知道黃梅戲的特點(dian)是(shi)(shi)什(shen)么嗎?人(ren)(ren)們對于他的藝術價值評論又(you)是(shi)(shi)什(shen)么呢(ni)?下(xia)面(mian)就(jiu)和小編一起來看(kan)看(kan)吧。
約(yue)從清乾(qian)隆(long)未期(qi)到辛亥(hai)革命(ming)前后。產(chan)生(sheng)和(he)流傳到皖(wan)、鄂、贛三省間(jian)的采茶調(diao)、江西調(diao)、桐城調(diao)、鳳陽歌,受(shou)當地(di)戲曲(青陽腔、徽(hui)調(diao))演出的影響,與蓮湘、高蹺、旱船等(deng)民間(jian)藝術形成結合,逐漸形成了(le)一(yi)些(xie)小戲。
進一(yi)步(bu)發展,又從(cong)一(yi)種(zhong)叫“羅(luo)漢樁(zhuang)”的曲藝形式和青陽腔與徽調吸收(shou)了演(yan)出(chu)內容(rong)與表(biao)現形式,于是(shi)產生了故事完整(zheng)的本(ben)戲。從(cong)小戲到本(ben)戲還有(you)一(yi)種(zhong)過渡形式,老藝人稱(cheng)之(zhi)為“串(chuan)戲”。所謂“串(chuan)戲”就是(shi)各自獨立而又彼此關連著(zhu)的一(yi)組小戲,有(you)的以事“串(chuan)”,有(you)的則以人“串(chuan)”。
“串戲(xi)”的情(qing)節比小戲(xi)豐(feng)富,出(chu)場的人物(wu)也突破(po)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fan)圍。其中(zhong)一些(xie)年齡(ling)大的人物(wu)需要(yao)用正旦、老生、老丑來扮(ban)演。這就(jiu)為本(ben)戲(xi)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第(di)二階段,是(shi)從(cong)辛亥革命到1949年。這一(yi)階段,黃(huang)梅戲(xi)(xi)演出(chu)活(huo)動漸漸職業化,并從(cong)農村草臺走上(shang)了城市舞臺。黃(huang)梅戲(xi)(xi)入城后(hou),曾與(yu)京劇(ju)合(he)班(ban),并在上(shang)海(hai)受到越劇(ju)、揚劇(ju)、淮劇(ju)和從(cong)北(bei)方(fang)來的評劇(ju)(時稱“蹦蹦戲(xi)(xi)”)的影響(xiang),在演出(chu)的內容與(yu)形式上(shang)都起了很(hen)大變化。編排、移植(zhi)了一(yi)批新劇(ju)目,其中有連(lian)臺本戲(xi)(xi)《文素臣(chen)》、《宏碧(bi)緣》、《華麗緣》、《蜜蜂記》等(deng)。
音樂方面,對傳統(tong)唱(chang)(chang)腔(qiang)進(jin)行初步改革,減少(shao)了(le)老腔(qiang)中(zhong)的(de)虛聲襯(chen)字,使之明快、流暢,觀眾易于聽懂所唱(chang)(chang)的(de)內容。取消了(le)幫腔(qiang),試用胡琴伴奏(zou)。表演(yan)方面,吸收融化了(le)京劇(ju)和(he)(he)其(qi)他(ta)兄弟劇(ju)種的(de)程式(shi)動作,豐富了(le)表現手段(duan)。其(qi)它如服裝、化妝和(he)(he)舞臺(tai)設(she)置,亦較農村(cun)草臺(tai)時有(you)所發展。
第三(san)階段,是1949至(zhi)今。1952年(nian),安慶黃梅戲(xi)藝(yi)(yi)人帶著(zhu)《打豬(zhu)草》、《藍橋會》等劇(ju)目到上海演(yan)出。幾(ji)十年(nian)來(lai)造就(jiu)了一大(da)批(pi)演(yan)員(yuan),除(chu)對黃梅戲(xi)演(yan)唱藝(yi)(yi)術有突出成(cheng)就(jiu)的嚴(yan)鳳英(ying)、王少(shao)舫等老一輩藝(yi)(yi)術家外(wai)(wai),中青(qing)年(nian)演(yan)員(yuan)馬蘭、韓再芬等相(xiang)繼(ji)在(zai)舞臺(tai)上、銀幕(mu)上和電視屏幕(mu)上展現了各自(zi)的英(ying)姿,引起了觀眾(zhong)的注視。嚴(yan)鳳英(ying)、王少(shao)航合演(yan)的《天仙配》,曾二度攝制(zhi)成(cheng)影片,轟動海內外(wai)(wai)。
黃梅戲的藝術特色:
在劇(ju)目方面,號稱“大(da)戲三十六本,小戲七(qi)十二折”。大(da)戲主要表現(xian)的(de)是當(dang)時人(ren)民對階級壓迫(po)、貧富(fu)懸殊的(de)現(xian)實(shi)不(bu)滿和(he)對自由(you)美好生(sheng)活的(de)向往。如《蕎麥記》、《告(gao)糧官》、《天(tian)仙配》等。小戲大(da)都表現(xian)的(de)是農村勞動者的(de)生(sheng)活片段,如《點大(da)麥》、《紡棉紗》、《賣斗(dou)籮》。
解(jie)放以后,先后整理(li)改編了(le)《天仙(xian)(xian)配(pei)》、《女駙(fu)馬(ma)》、《羅帕記》、《趙桂英》、《慈母淚》、《三搜國(guo)丈府》等一批(pi)大小傳統劇目,創作了(le)神(shen)話劇《牛郎(lang)織(zhi)女》、歷史劇《失刑斬》、現代戲《春暖花開(kai)》、《小店(dian)春早》、《蓓(bei)蕾初開(kai)》。其中《天仙(xian)(xian)配(pei)》、《女駙(fu)馬(ma)》和(he)《牛郎(lang)織(zhi)女》相繼搬上銀幕,在國(guo)內外產(chan)生了(le)較大影響(xiang)。嚴鳳英、王少舫、吳瓊、馬(ma)蘭是黃梅戲的(de)著名演員。
黃梅戲(xi)(xi)的(de)類別主要有花腔和平(ping)詞。花腔以演(yan)小戲(xi)(xi)為主,富生活(huo)氣息和民(min)歌(ge)風味。平(ping)詞,正(zheng)本戲(xi)(xi)中的(de)主要唱腔,常用(yong)大段的(de)敘述(shu)、抒情,韻味豐富,如行云流(liu)水。
黃梅戲有(you)兩(liang)(liang)大聲腔(qiang)體(ti)系(xi)(xi)———花(hua)腔(qiang)體(ti)系(xi)(xi)、平詞體(ti)系(xi)(xi)。花(hua)腔(qiang)體(ti)系(xi)(xi)脫(tuo)胎于(yu)(yu)民歌小調(diao),屬曲牌體(ti)。平詞體(ti)系(xi)(xi)淵源(yuan)于(yu)(yu)高腔(qiang)、彈詞、羅漢樁、道情(qing)、吹(chui)腔(qiang)、徽(hui)調(diao)、京劇(ju)等(deng)聲腔(qiang),屬板腔(qiang)體(ti)。這兩(liang)(liang)大聲腔(qiang)體(ti)系(xi)(xi),都植根于(yu)(yu)安慶地區(qu)的(de)聲腔(qiang)土壤。黃梅戲表演形(xing)式(shi),在學習借鑒昆曲、京劇(ju)、徽(hui)劇(ju)等(deng)大劇(ju)種的(de)基礎(chu)上,逐(zhu)步形(xing)成了自(zi)己的(de)風格。
早(zao)期黃(huang)(huang)梅(mei)(mei)戲(xi)從(cong)業人(ren)(ren)(ren)(ren)員(yuan)中,有(you)成就、且有(you)史料記載(zai)的黃(huang)(huang)梅(mei)(mei)戲(xi)老藝人(ren)(ren)(ren)(ren),絕大(da)部分都是(shi)安(an)(an)慶(qing)(qing)地區的人(ren)(ren)(ren)(ren)。例如蔡(cai)仲(zhong)賢(已知最早(zao)黃(huang)(huang)梅(mei)(mei)戲(xi)演員(yuan),生于(yu)1821年,望江(jiang)縣(xian)(xian)人(ren)(ren)(ren)(ren)),胡(hu)(hu)普伢(ya)(最早(zao)黃(huang)(huang)梅(mei)(mei)戲(xi)女演員(yuan),生于(yu)1821年,太湖縣(xian)(xian)人(ren)(ren)(ren)(ren))、洪海波(潛(qian)山縣(xian)(xian)人(ren)(ren)(ren)(ren))、葉炳池(東(dong)至縣(xian)(xian)人(ren)(ren)(ren)(ren))、咎雙(shuang)印(懷寧縣(xian)(xian)人(ren)(ren)(ren)(ren))、胡(hu)(hu)玉亭(望江(jiang)縣(xian)(xian)人(ren)(ren)(ren)(ren))、龍昆玉(望江(jiang)縣(xian)(xian)人(ren)(ren)(ren)(ren))、程積善(shan)(貴池縣(xian)(xian)人(ren)(ren)(ren)(ren))、查文艷(懷寧縣(xian)(xian)人(ren)(ren)(ren)(ren))、丁(ding)永(yong)泉(quan)(懷寧縣(xian)(xian)人(ren)(ren)(ren)(ren))、潘澤海(安(an)(an)慶(qing)(qing)市(shi)人(ren)(ren)(ren)(ren))、嚴鳳英(桐(tong)城羅(luo)嶺人(ren)(ren)(ren)(ren))等,他(ta)們之間都有(you)師承關系。
建國前,黃梅戲(xi)沒有文人介入,演出的(de)百余本大小(xiao)傳(chuan)統劇(ju)目,絕大部(bu)分都是移植于青陽腔(qiang)、岳西(xi)高腔(qiang)、京劇(ju)和(he)徽劇(ju)。
通過(guo)以上對黃(huang)(huang)梅戲(xi)聲腔(qiang)形(xing)成的(de)(de)(de)探討,劇(ju)目積淀的(de)(de)(de)溯源(yuan),演員師承關系(xi)的(de)(de)(de)覓蹤以及黃(huang)(huang)梅戲(xi)歷史沿革發展的(de)(de)(de)總體把握,我們對黃(huang)(huang)梅戲(xi)劇(ju)種的(de)(de)(de)發展概貌,有了一個(ge)較為清晰的(de)(de)(de)認識。
黃梅(mei)戲的(de)(de)(de)(de)源(yuan)頭(tou)就(jiu)在安(an)(an)慶(qing)(qing)地區,黃梅(mei)戲誕生于(yu)(yu)(yu)安(an)(an)慶(qing)(qing)地區,成(cheng)長于(yu)(yu)(yu)安(an)(an)慶(qing)(qing)地區,興(xing)盛于(yu)(yu)(yu)安(an)(an)慶(qing)(qing)地區。聲腔系統(tong)是一(yi)個劇(ju)種(zhong)(zhong)(zhong)的(de)(de)(de)(de)重要(yao)標(biao)志,任何一(yi)個劇(ju)種(zhong)(zhong)(zhong)和隸屬(shu)于(yu)(yu)(yu)這(zhe)個劇(ju)種(zhong)(zhong)(zhong)的(de)(de)(de)(de)聲腔系統(tong)的(de)(de)(de)(de)形(xing)成(cheng),都有一(yi)個不(bu)(bu)斷吸(xi)納(na)、借(jie)鑒(jian)、融(rong)會、揚棄、改造(zao)、流傳、不(bu)(bu)斷適應觀(guan)眾審(shen)美需求、艱難復(fu)雜的(de)(de)(de)(de)積累創造(zao)的(de)(de)(de)(de)過程(cheng)。在這(zhe)個不(bu)(bu)斷走向成(cheng)熟的(de)(de)(de)(de)過程(cheng)中,一(yi)定會有與本劇(ju)種(zhong)(zhong)(zhong)在文化背(bei)景、人文環境、審(shen)美趨向、生活習俗等方面,存在著淵源(yuan)關系的(de)(de)(de)(de)某(mou)一(yi)種(zhong)(zhong)(zhong)或某(mou)幾種(zhong)(zhong)(zhong)音(yin)樂素材(cai),是本劇(ju)種(zhong)(zhong)(zhong)的(de)(de)(de)(de)重要(yao)養分,從而加速了(le)這(zhe)個劇(ju)種(zhong)(zhong)(zhong)的(de)(de)(de)(de)形(xing)成(cheng)。
如果我們將(jiang)一(yi)個劇(ju)種比喻成一(yi)條(tiao)江河(he),那(nei)么(me),對于(yu)催(cui)生這一(yi)劇(ju)種成熟的(de)某(mou)一(yi)種或某(mou)幾(ji)種音(yin)樂素(su)材,只能算是沿途匯(hui)入那(nei)條(tiao)江河(he)的(de)支流。黃梅(mei)(mei)(mei)戲之于(yu)黃梅(mei)(mei)(mei)采茶(cha)調(diao)的(de)關系,就如同江河(he)與支流的(de)關系,黃梅(mei)(mei)(mei)采茶(cha)調(diao)是促成黃梅(mei)(mei)(mei)戲成熟的(de)重要因素(su),但(dan)決不是黃梅(mei)(mei)(mei)戲的(de)源頭。
黃梅(mei)(mei)戲源頭的歷史記(ji)載(zai)陸洪非先生在《黃梅(mei)(mei)戲源流》一書(shu)中,對黃梅(mei)(mei)戲的源頭列舉了(le)幾種傳(chuan)說(shuo)。
傳說之—:“黃梅戲是在(zai)‘懷(huai)寧(ning)腔(qiang)’的(de)(de)基礎上發展起來(lai)的(de)(de)。??每當(dang)春種秋收之時(shi),農(nong)民(min)們(men)慣唱‘懷(huai)調山(shan)歌’來(lai)歌頌自己勞動的(de)(de)豐收。這種民(min)間優(you)美抒情的(de)(de)山(shan)歌小調,統稱為‘懷(huai)寧(ning)調’。”
傳說之(zhi)二“??黃(huang)梅(mei)戲起源于安徽安慶地區(qu)。從前每逢(feng)黃(huang)梅(mei)季節,常(chang)常(chang)洪(hong)水成災,四鄉(xiang)農(nong)民為了祈求豐(feng)年,就在(zai)這個時候舉辦迎神賽會(hui),會(hui)上出現各種歌舞(wu)演(yan)唱,在(zai)這種歌舞(wu)演(yan)唱形(xing)式的基礎上產生(sheng)的一種戲曲形(xing)式,因(yin)與黃(huang)梅(mei)季節有(you)關,故名曰‘黃(huang)梅(mei)調’。”
傳說之三:“黃(huang)梅戲源于湖北(bei)黃(huang)梅縣(xian)的民歌小調即黃(huang)梅采茶調。”
以上三種(zhong)傳(chuan)說,我認(ren)為前兩(liang)種(zhong)傳(chuan)說較為符合歷史真(zhen)實,后一種(zhong)傳(chuan)說就顯(xian)得(de)牽強附會,很多人因(yin)為黃(huang)梅戲和黃(huang)梅縣同(tong)字同(tong)音而趨同(tong)黃(huang)梅戲源于(yu)黃(huang)梅縣的說法。當(dang)然,一些(xie)專家也(ye)曾從音樂、劇目(mu)、師承(cheng)的層面進行分析、推論(lun),認(ren)為黃(huang)梅戲源于(yu)黃(huang)梅采茶調(diao),但提出的論(lun)據、論(lun)點不具有說服力,他(ta)們也(ye)坦(tan)承(cheng)由(you)于(yu)可供(gong)借鑒的資料匱乏(fa),所以,無法最(zui)終形成定論(lun)。
至于(yu)黃(huang)(huang)梅(mei)戲到底源(yuan)于(yu)何處,很少人有(you)興趣去(qu)探討研(yan)究。這既(ji)有(you)年(nian)代久遠,原本(ben)就缺少文字資料,一(yi)些了(le)解情況的老藝人也相繼(ji)去(qu)世,又無(wu)經(jing)費支持的原因,也與人們普遍對黃(huang)(huang)梅(mei)戲起(qi)源(yuan)持漠(mo)視態度(du)有(you)關(guan)。
【結束語(yu)】我以為,黃梅戲(xi)(xi)經(jing)過一代(dai)又(you)一代(dai)人艱苦卓絕(jue)的創造發展,已從(cong)一個名不見(jian)經(jing)傳(chuan)的民間(jian)小戲(xi)(xi),一躍成為全國(guo)著名劇種(zhong),且在戲(xi)(xi)曲整(zheng)體萎(wei)縮的形(xing)勢下(xia),依然保持著一種(zhong)良好的發展態(tai)勢,這得益(yi)于(yu)黃梅戲(xi)(xi)的通俗化、大眾(zhong)化的藝術品格和(he)與時俱進的創新(xin)精神。
【黃梅戲有哪些經典曲目】
楊劇:,《香羅帶》、《玉晴蜓》、《喜娟》、《修匾記》《上金山》、《八姐打店》、《偷詩》《十二寡婦征西》、《珍珠塔》、《洪宣嬌》、《紂王與妲己》、《碧血揚州》、《梁祝哀史》、《八姐打店》、《皮匠掛帥》、《秦香蓮》、《海公大紅袍》京劇:《霸王別姬》《游園驚夢》《鎖麟囊》《沙家浜》《逍遙津》《打漁殺家》:《失空斬》、《鎖麟囊》、《貴妃醉酒》、《紅鬃烈馬黃梅戲:《天仙配》、《牛郎織女》、《槐蔭記》、《女駙馬》、《孟麗君》、《夫妻觀燈》、《打豬草》、《柳樹井》、《藍橋會》、《路遇》、《王小六打豆腐》、《小辭店》、《玉堂春》
【黃梅戲(xi)的起(qi)源和發展】
黃梅戲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戲曲劇種。在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蘇、等省以及地區亦有黃梅戲的專業或業余的演出團體,受到廣泛的歡迎。黃梅戲原名“黃梅調”,是十八世紀后期在皖、鄂、贛三省毗鄰地區形成的一種民間小戲。其中一支逐漸東移到安徽省桐城市為中心的安慶地區,與當地民間藝術相結合,用當地語言歌唱、說白,形成了自己的特點,被稱為“桐城歌”或“黃梅歌”。這就是今日黃梅戲的前身。
黃梅戲在劇目方面,號稱“大戲三十六本,小戲七十二折”。大戲主要表現的是當時人民對階級壓迫、貧富懸殊的現實不滿和對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如《蕎麥記》、《告糧官》、《天仙配》等。小戲大都表現的是農村勞動者的生活片段,如《點大麥》、《紡棉紗》、《賣斗籮》。
解放以后,先后整理改編了《天仙配》、《女駙馬》、《羅帕記》、《趙桂英》、《慈母淚》、《三搜國丈府》等一批大小傳統劇目,創作了神話劇《牛郎織女》、歷史劇《失刑斬》、現代戲《春暖花開》、《小店春早》、《蓓蕾初開》。其中《天仙配》、《女駙馬》和《牛郎織女》相繼搬上銀幕,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嚴鳳英、王少舫、吳瓊、馬蘭是黃梅戲的著名演員。
黃梅戲已成為深受全國觀眾喜愛的著名劇種。黃梅戲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早期叫黃梅調,是“自唱自樂”民間藝術。
起源的爭議
黃梅戲源頭的歷史記載陸洪非先生在《黃梅戲源流》一書中,對黃梅戲的源頭列舉了幾種傳說。
傳說之一:安徽桐城的《桐城歌》是明朝時就傳到黃梅(湖北——引者按)一帶。 黃梅戲是由桐城縣羅家嶺的嚴鳳英唱紅的,羅家嶺的方言是純正的桐城腔。由此可見桐城是黃梅戲的源頭最具說服力。
傳說之二∶“黃梅戲是在‘懷寧腔’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每當春種秋收之時,農民們慣唱‘懷調山歌’來歌頌自己勞動的豐收。這種民間優美抒情的山歌小調,統稱為‘懷寧調’。”不過沒有多少證據證明。
傳說之三∶“……黃梅戲起源于安徽安慶地區。從前每逢黃梅季節,常常洪水成災,四鄉農民為了祈求豐年,就在這個時候舉辦迎神賽會,會上出現各種歌舞演唱,在這種歌舞演唱形式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戲曲形式,因與黃梅季節有關,故名曰‘黃梅調’。”這種說法也沒有多少說服力。
傳說之四∶“黃梅戲源于湖北黃梅縣的民歌小調即黃梅采茶調。”這種可能性也不大。
現代學者也對黃梅戲源頭多有探索,如最近戲曲理論家吳福潤先生在《黃梅戲藝術》雜志撰文,認為桐城(安慶)“黃梅戲”全國聞名,而黃梅戲起源地眾說紛紜,部分人認為起源于湖北黃梅縣,可能是由“黃梅”二字引來的誤傳。“黃梅戲”的確與“黃梅”二字息息相關,但“黃梅”不是人們所說的黃梅縣,而是“黃梅山”。傳說此山很久以前寒冬臘月山上遍開黃色梅花而得名,后來“黃梅”逐漸稀少,現在偶爾也能發現“黃梅”蹤跡。
也有部分江西民間傳說,黃梅戲起源于江西,但此種說法基本未為大眾認可。
也有人認為如今爭論黃梅戲屬于哪兒已沒有意義,對黃梅戲的發展沒有任何推動作用。他建議專家學者將更多注意力放在黃梅戲本身的發展規律上,進一步鞏固、提高黃梅戲這個地方劇種在當今戲曲領域中的地位。
中國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黃梅戲保護區域是安徽省的安慶市和湖北省的黃梅
【黃(huang)梅(mei)戲(xi)的藝(yi)術特點】
黃梅戲的唱腔屬板式變化體,有花腔、腔、主調三大腔系。花腔以演小戲為主,曲調健康樸實,優美歡快,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民歌小調色;腔曲調歡暢,曾在花腔小戲中廣泛使用;主調是黃梅戲傳統正本大戲常用的唱腔,有平詞、火攻、二行、三行之分,其中平詞是正本戲中最主要的唱腔,曲調嚴肅莊重,優美大方。黃梅戲以抒情見長,韻味豐厚,唱腔純樸清新,細膩動人,以明快抒情見長,具有豐富的表現力,且通俗易懂,易于普及,深受各地群眾的喜愛。在音樂伴奏上,早期黃梅戲由三人演奏堂鼓、鈸、小鑼、大鑼等打擊樂器,同時參加幫腔,號稱“三打七唱”。中華人民成立以后,黃梅戲正式確立了以高胡為主奏樂器的伴奏體系。
黃梅戲唱腔委婉清新,分花腔和平詞兩大類。花腔以演小戲為主,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民歌風味,多用“襯詞”如“呼舍”、“喂卻”之類。有“夫妻觀燈”、“藍橋會”、“打豬草”等;平詞是正本戲中最主要的唱腔,常用于大段敘述,抒情,聽起來委婉悠揚,有“梁祝”、“天仙配”等。現代黃梅戲在音樂方面增強了“平詞”類唱腔的表現力,常用于大段抒情、敘事,是正本戲的主要唱腔;突破了某些“花腔”專戲專用的限制,吸收民歌和其他音樂成分,創造了與傳統唱腔相協調的新腔。黃梅戲以高胡為主要伴奏樂器,加以其它民族樂器和鑼鼓配合,適合于表現多種題材的劇目。
一、唱腔
黃梅戲唱腔有三種形式:主腔、花腔、三腔(“腔”、“仙腔”、“陰司腔”三種腔體的統稱)。
黃梅戲的主腔
主腔是黃梅戲傳統唱腔中最具戲劇性表現力的一個腔系。它以板式變化體(或稱板腔體)為音樂結構的原則,正是這一主要特點使它區別于曲牌聯綴體(或稱曲牌體)的“花腔”以及兼有兩種體制特征的“三腔”。
主腔并不意味著在黃梅戲的所有劇目中每每為主。實際上,花腔小戲基本上不用主腔,有些大戲也并非以主腔為主,之所以把這一腔系稱作主腔,是就它的音樂形態及音樂表現功能而言的。另外,從黃梅戲音樂發展史來看,主腔也晚于花腔和三腔。這一發展過程又與劇目從獨角戲、兩小戲、三小戲發展到串戲而最終能演整本大戲的歷程相吻合。因此,可以認為:主腔是黃梅戲發展到成熟階段的產物。它的出現,標志著黃梅戲音樂的基本風格的框定。
黃梅戲的花腔
黃梅戲源于民間歌舞。山野村夫的勞動之歌,婦孺皆知的里巷歌謠,燈會社火之中的歡歌勁舞,是黃梅戲活潑的源頭。黃梅戲在形成第一個階段性成果——兩小戲、三小戲的進程中,也形成了百余首小曲雜調的“花腔”腔系。花腔從民歌中來,但作用已與民歌不大一樣。它已經從田頭走上舞臺,從隨口而歌進入到規定的戲劇情境,傳達角色的心聲。今天所見的花腔小調,無論它與民歌有多大程度的類似,但它確已經歷過戲劇浪頭的打磨,具備了戲劇性音樂的某些特質,是一種民歌式的曲牌體制。
1.花腔的藝術特點
花腔的藝術特點體現在調式色的明朗化、表情達意的質樸化、節奏律動的舞蹈化、旋律線條的口語化、唱詞結構的襯字(詞)化等方面。
花腔是一個調式豐富的腔系。有典型的五聲宮、商、角、徵、羽調式,還有運用偏音的五聲性的六聲調式等。花腔不同的調式色并不導致表情上的巨大反差。無論是大調性質的宮、徵調式,還是屬于小調性質的羽、角、商調式,既不用于表現昂揚豪邁之剛烈,也洋用于表現悲戚愁苦之柔弱,在節奏律動的驅使下,在旋律線條的跌宕起伏中,它們充滿著歡愉之情,諧謔之趣,似乎一切都很透明,一切都很樂觀,紛繁的調式只不過是增添色而已。花腔這種求輕盈不求沉重,尚樂天而不淪于穩如泰山唐的表情傾向,成為黃梅戲的音樂乃至整個黃梅戲藝術不得不留意的基本品質。
表情達意的質樸化也是花腔的一個特點,從唱詞看,狀物言情都以快人快語、詼諧逗趣見長。如《逃水荒》中“小小竹竿三尺長,安幾個銅錢響丁當”,名字叫“蓮廂”和《夫妻觀燈》中“長子來看燈,他擠得頭一伸。矮子來看燈,他擠在人網里蹲。胖子來看燈,他擠得汗淋淋。瘦子來看燈,他擠成一把筋”都是例證。從音樂看,簡潔的樂匯、自然的語勢、密集型的字位安排、結合成朗朗上口的旋律,既樸素又大方。
花腔的節奏具有民間舞蹈的律動。它用鑼鼓伴奏,流暢的“長槌”,梧合人物上場下場,“花腔二槌”、“花腔四槌”、“花腔六槌”緊貼著唱腔的各個部位,或作入頭,或作過門,令表演者和觀眾都有按捺不住的動感。
花腔的旋律線條非常口語化。它不僅符合當地方言的調值,還將人們說話時的鑼輯重音以及有意強調某一字的語勢都表達出來。花腔的百余首曲調,來自很多地方,如“蓮花”、“鳳陽歌”來自北方,“鮮花調”來自江南,這些曲調在流變的過程中,語言因素帶來的變異是十分明顯的,因此,花腔旋律的口語化,是統一花腔的風格的重要環節。
花腔在唱詞中常大幅度采用襯字襯詞,有些曲調甚至有“本末倒置”的現象,如“汲水調”,表意性的詞只有“走出門來抬頭看,三條大路走中間,奴家的小情歌”20個字,而加進襯詞就成了“走出門來咦么郎當,抬頭看呀么郎當,三條大路嗨嗨咦兒嗬嗨嗨呀兒嗬走中間,咦么郎當,郎得兒郎當,郎得兒郎當,唆兒嘞,唆兒嘞,嗨嗨咦嗨荷,唆兒嘞,奴家的小情哥。”需要說明的是,很多花腔的襯詞都是曲調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擴大了曲式結構,使短小的兩句頭、三句頭小曲豐富起來。襯字的非表意性,為演唱者留出空白,可以任意點染自己所認可的情緒。當然過多的襯字襯詞使本來易懂的詞意變得難以捕捉,這是不必諱言的。
2.花腔的用法
從兩上視角觀察花腔的用法,一是花腔與小戲、串戲、大戲的關系,一是花腔各個小曲的自身變化以及小曲間的連接。
花腔與小戲密不可分,它幾乎是小戲的代名詞。在小戲中,花腔絕大多數是專曲專用,如“對花調”、“打豬草調”專用于《打豬草》,“開門調”、“觀燈調”專用于《夫妻觀燈》等。花腔在串戲中的使用情形與小戲類似。在大戲中,花腔僅作插曲。
花腔的某一首曲調自身的變化,主要是旋律線的變化。這種變化常常發生在小戲或串戲中的生旦角色共用一首曲調的時候。如“打豬草調”,陶金花上場與金小毛上場所唱略有差別。女腔在一個八度內活動,在樂句的開頭每每碰撞最高音,旋律活潑而流暢;男腔則避開女腔的高音,在六度音域內活動,旋律線條較顯棱角。
花腔屬于曲牌聯綴體。常見的是一出戲(小戲或串戲的一折)用1~2首花腔小曲。這些小曲用原型,也產生一些變體,在旋律上或板式上有所拓展。如《打豬草》前半部用“打豬草調”,男女腔有旋律上的差異。后半部用“對花調”,先是男女對唱齊唱,繼而發展成“對花調對板”。花腔在小戲中也偶爾用一下主腔,如《打豬草》就是在“對花調對板”之后,忽然終止在“平詞切板”上。但更多的時候,花腔是與三腔中的腔聯用。如小戲《夫妻觀燈》,開始處便用了五聲徵調式的男腔,接著,是女腔為主男腔附和的五聲宮調式的“開門調”。以后是“開門調”自身再產生板式變化,形成兩首不同的“開門調對板”。當唱到“這班燈過了身,那廂又來一班燈”時,“腔”的變體與“開門調”結合,構成了內含調性調式變化的“觀燈調”,“觀燈調”進而引入“腔對板”擴大曲體,并強烈地維持著腔的調式調性,全劇最后結束在男女合唱的腔上。設腔因素為A,開門調因素為B,二者結合為C,《夫妻觀燈》粗略的線條變是A-B-C-A-C-A,像這種材料集中、對比得當的結構手法,至今仍然是不可忽略的優秀傳統。
3.花腔的戲劇音樂特征
花腔的戲劇音樂特征表現在角色意識的覺醒和板式手段的運用上。
如果把塑造典型的“這一個”音樂形象定位在戲曲音樂表現的最高層次,那么,居中的是程式化的行當唱腔,而處于最下層的是角色意識初萌的產物——簡單的男女分腔。導致這種區分的動機很明顯,即讓人們從音樂中聽出角色的性別來。
板式變化的手段對花腔的滲透,導致戲劇音樂特征進一步顯現。如“對花調”、“開門調”、“討學俸調”都演化出對板形式,這就增強了花腔的敘事功能。另外,被認為是青陽腔主要特色的滾調,也以滾板形式進入花腔,如“開門調”于一板一眼中夾入有板無眼的滾板唱腔,使音樂有了疏密快慢的比照,強化了戲劇性表現。
黃梅戲的三腔
三腔是“腔”、“仙腔”、“陰司腔”三種腔體的統稱。
三腔有許多共同點。首先,三腔在音樂體制上綜合了曲牌體和板腔體的因素,呈現出“準板腔體”的狀態。三腔各自擁有一個基本腔體,腔、仙腔為四句體,它們的字位安排、復句位置、鑼鼓的用法都較固定,具有曲牌體的定格之感。但三腔的每一腔體都派生出對板或數板,還形成一些補充腔句,因此,三腔也有板腔體的特點。其次,在男女分腔上,三腔既不同于主腔的男女腔轉調相連,也不同于大多數花腔小曲的男女腔同腔同調演唱,而是男女腔在旋律上差別較大,容易區別開來。再者,在戲劇性表現功能上,三腔兼有抒情性敘事性表現能力。
三腔是一組情趣各異的姊妹腔,它們的不同之處也很顯見。如三腔的來源各不相同。腔,又稱“打調”,它由花腔小曲逐漸演變而成。仙腔也稱作“道腔”、“道情”,產生于當地的道教音樂,直接進入黃梅戲或先由青陽腔吸收后由黃梅戲傳承。陰司腔又叫“還魂腔”,來自青陽腔,故又叫“陰司高腔”。三腔的表情及用途也不同:腔表達光高采烈的喜慶之情;而男仙腔則有舒展灑脫的氣度,通過特殊唱法的處理,還可以獲得奇異的喜劇色或表達傷感的情緒,陰司腔是一個表現沉郁的腔體,原為劇中亡靈或行將辭世的角色抒發悲傷的情感所用,其言戚戚,其音哀哀,恍若進入陰曹地府一般。另外,三腔的調式及句式不盡相同。腔、仙腔有五聲徵調式、六聲徵調式兩種,陰司腔則是五聲商調式。
1.腔
腔的基本結構是四句體。男女腔保持著共同的調式、共販字位安排及共同的核心樂匯,但旋律線是男腔走低女腔走高。腔以“花腔六槌”作入頭,第二句唱腔后用“花腔四槌”,第三句唱腔后用“花腔二槌”,一段腔唱完可用“花腔一槌”終止唱段。腔為徵調式,大多是五聲,偶爾旨直變宮音。四句腔的落音分別是5 5 6 5。老的腔與黃梅采茶戲有所近似是而非,四句腔的落音是6 5 6 5或1 5 6 5。從音樂的材料上看,腔的第二句與第四句旋律十分相近,而第三句則具有較強的展開性,形成ABCB的“起承轉合”結構。
腔的輔助板式有對板和散板,均由上下句構成,這種板式或一人獨唱或二人對唱,增強了腔的敘事功能。對板為一板一眼,詞格有五字句和七字句。對板常以下句與具有“轉”句功能的腔第三句相接,也可從腔第二句后接對板上句或唱完一段腔后再接對板等。腔的補充腔句主要有“邁腔”,它代替第三句的位置。邁腔的句幅比第三句短小,落音在1上,具有新鮮感,以增加音樂的動力。腔的落板方式是將結束句放慢,利用速度的遞減形成緩沖以造成終止。另外,腔也停留在“切板”上,“切板”的旋律與“平詞切板”大致相同。
腔的四句基本腔,有時因唱詞增多而有擴展。擴展的方式,一種是用“句首加帽”的方法增加行腔,另一種是增加滾唱。如在《三字經》的丑唱腔中,因唱詞句式多變而生出有板無眼的流水落石出板和滾唱并用的大段腔來。腔這種一曲多變的實例,說明黃梅戲傳統唱腔的自由度歷來就很大。當某種腔調形成了大致的框格,聰明的藝人們便“據本而衍文”,從這個邊緣不十分清晰的本體中,孳生出許許多多的枝節,甚至可以大增大減,演化出多種多樣的變體來。這大概就是民間藝人創腔的“作曲法”。
腔因其音樂體制介乎于主腔、花腔之間,與它們的聯用也很常見,尤其是小戲中,腔與花腔聯用更為頻繁。另外,在早期的花腔小戲演出中,腔常常用于“打”。所謂打是游離于戲外的一種籌款活動,是藝人獲取收入的一種手段。且不論某些藝人在討中不免有庸俗的表演,但用于打的曲調當是受眾最廣,最能代表劇種特色的唱腔。藝人們“百里挑一”選擇了它,觀眾也“百聽不厭”接納了它,那么腔的形態特征及音樂情趣當是不可忽略的。
2.仙腔
仙腔的基本結構也是四句體,但形態比腔復雜。仙腔要在兩個部位重復唱詞,一處是第一句詞(七字句)的后三個字,另一處是第四句詞全句重復。這樣,四句腔的長度變得參差不齊,在腔體內部造成了有的樂句一掠而過,有的樂句則重點強調的對比效果。
復句是高腔中常見的一種表現手段,在岳西高腔中,復句是要在抄本上用符號予以圈點的,足見藝人們對它的重視。高腔的復句,被重復的唱詞披以新的旋律,腔幅也有很大變化,這與黃梅戲仙腔的復句手法相似。
仙腔也用花腔鑼鼓。以“花腔六槌”作入頭,可用“花腔一槌”收束,這與腔相同。但內戰腔在第一句腔與三字復句之間夾入“花腔二槌”,在三字復句之后,接以“花腔四槌”,形成頭一句唱詞(含復句)緊鑼密鼓的狀態,這與腔中鑼鼓較平均的用法有很大差別。在老的仙腔中還運用幫腔,并且用“靠腔鑼”隨腔擊節,這些都是高腔特點的留存。仙腔的輔助板式有數板(也稱對板),是將仙腔腔體內的第二、第三兩句予以變化重復而形成的上下句結構。
仙腔的補充腔句有“邁腔”,句幅及落音與“腔邁腔”相同。
仙腔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它可以用變奏的手法形成不同變體,這種變體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稍有不同,而是有相當大的表情差異。以《天仙配》為例,當眾仙女偷偷來至天河,觀看人間美景時,表現她們得到解脫后的愉悅之情用的是仙腔;當七仙女小施法術,令千年槐樹開口講話時,配合這一神奇場面的是音色古怪、口吻夸張的男唱仙腔;當董永得知七仙女將被迫離他而去,那棵曾作媒證的老槐樹也啞口無言,不能相助時,他傷心至極地唱著:“啞木頭,啞木頭,連叫三聲,不開口。”這里用的還是仙腔。如此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人物,反差極大的情感表達都以仙腔來體現。
3.陰司腔
陰司腔是黃梅戲主腔諸腔體與三腔之中表情最單一,拖腔最充足的腔體。專用于傷感之時,上下兩句腔的末字上都有四到六小節的行腔。
陰司腔一波三折,凄婉動人,極善表達劇中人如死灰的絕望之情。由于這一特點,它常與主腔聯用,以補足主腔的悲腔塊面。
陰司腔是五聲商調式。調式色既不同于主腔,也不同于腔,仙腔。這使它兀立于群腔之中,很容易分辨。
陰司腔因其腔句長大和表情單一而不宜反復使用,一般只用一遍就轉入輔助板式和補充腔句。從這里似乎可以“悟”出板腔體對上下句的要求:它排斥非敘事性的過長拖腔,同時,它對表情的要求取“中性色”,那些情緒過于偏狹而不易更動的腔句,不宜用作變奏的原型,也就不配作上下句的母體。
陰司腔的輔助板式是上下句結構的數板,具有較強的敘事能力,它的旋律來自陰司腔的上下句,同樣也是五聲商調式。陰司腔的補充腔句是“陰司邁腔”,它的結構及落音與腔邁腔、仙腔邁腔同。常用于陰司腔上下句之后,以轉向陰司腔數板或別的腔體。由于表情的互通,陰司腔常與“哭介”結合在一起,傷情之處,輔以哭喊的音調,以求更強烈的悲劇性表現。
二、語言
黃梅戲語言以安慶地方語言為基礎,屬北方方言語系的江淮方言。其特點為——唱詞結構在整本戲多為七字句和十字句式。七字句大多是二、二、三結構,十字句大多是三、三、四結構。有時可根據需要以七字、十字句為框架,字數可壓縮或增擴,曲調則常使用垛句。花腔小戲的唱詞靈活多變,有三至七字不等,中間常夾雜多種口語化無詞意的字。句數不一定為偶數有時奇數句重復最后一句便成偶數。唱念方法均用接近普通話的安慶官話唱念。整本戲中用韻母念、官話唱,小戲說白則用安慶地方的鄉音土語,唱腔仍用官話唱。 黃梅戲角色行當的體制是在“二小戲”、“三小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上演整本大戲后,角色行當才逐漸發展成正旦、正生、小旦、小生、小丑、老旦、奶生、花臉諸行。辛亥革命前后,角色行當分工被歸納為上四腳和下四腳。上四腳是:正旦(青衣)、老生(白須)、正生(黑須)、花臉;下四腳是:小生、花旦、小丑、老旦。行當雖有分工,但很少有人專工一行。民國十九年(1930)以后,黃梅戲班社常與徽、京班社合班演出。由于演出劇目的需要,又出現了刀馬旦、武二花行當,但未固定下來。當時的黃梅戲班多為半職業性質,一般只有三打、七唱、箱上(管理服裝道具)、箱下(負責燒茶做飯)十二人。行當搭配基本上是正旦、正生、小旦、小生、小丑、老旦、花臉七行。由于班社人少,演整本大戲時,常常是一個演員要兼扮幾個角色,因而在黃梅戲中,戲內角色雖有行當規范,但演員卻沒有嚴格分行。
正旦:多扮演莊重、正派的成年婦女,重唱工,表演要求穩重大方。所扮演的角色如:《蕎麥記》中的王三女、《羅帕記》中的陳賽金、《魚網會母》的陳氏等。
小旦:又稱花旦,多扮演活潑、多情的少女或少婦,要求唱做并重,念白多用小白(安慶官話),聲調脆嫩甜美,表演時常執手帕、扇子之類,舞動簡單的巾帕花、扇子花。所扮演的角色如:《打豬草》中的陶金花、《游春》中的趙翠花、《小辭店》中的劉鳳英等。演出整本大戲后,小旦行又細分出閨門旦及專演丫鬟的行當“捧托”。旦行是黃梅戲的主要行當,舊有“一旦挑一班”之說。
小生:多扮演青少年男子,用大嗓演唱,表演時常執折扇。扮演的角色如:《羅帕記》的王科舉、《春香鬧學》的王金榮、《女駙馬》的李兆廷、《天仙配》的董永等。
小丑:分小丑、老丑、女丑(旦)三小行。在黃梅戲中,丑行比較受歡迎。為幫助演出,小丑常拿著一根七、八寸長的旱煙袋,老丑則拿著一根二、三尺長的長煙袋,插科打諢,調節演出氣氛。扮演的角色如《打豆腐》中的王小六、《釣蛤蟆》中的楊三笑等。
老旦:扮演老年婦女,在戲中多為配角。如《蕎麥記》中的王夫人。
花臉:黃梅戲中花臉專工戲極少,除在大本戲中扮演包拯之類的角色外,多扮演惡霸、寨主之類的角色,如《賣花記》的草鼎、《二龍山》的于彪等。
正生:又稱掛須,有黑白須之分,一般黑須稱正生,白須稱老生。重唱念,講究噴口、吐字鏗鏘有力。所扮演的角色如:《蕎麥記》中的徐文進、《告經承》的張朝宗、《桐城奇案》的張柏齡等。 黃梅戲最初只有打擊樂器伴奏,即所謂“三打七唱”。抗日戰爭時期,曾嘗試用京胡托腔;后又試用二胡伴奏,但都未能推廣。到建國初期,才逐漸確定用高胡作主要伴奏樂器,并逐步建立起以民族樂器為主、西洋樂器為輔的混合樂隊,以增強音樂表現力。
伴奏(zou)鑼(luo)(luo)鼓(gu)最初只有(you)大鑼(luo)(luo)、小鑼(luo)(luo)、扁(bian)形圓(yuan)鼓(gu),被稱作(zuo)“三打七唱(chang)”,即3人演(yan)奏(zou)打擊樂器并參(can)加(jia)幫(bang)腔(qiang)、7人演(yan)唱(chang)。以后執堂鼓(gu)者(zhe)(zhe)又(you)兼(jian)奏(zou)竹(zhu)根節和(he)(he)鈸,3名(ming)伴奏(zou)者(zhe)(zhe)分別坐在上(shang)場門內外(wai)側和(he)(he)草臺正中(zhong)(奏(zou)鼓(gu)者(zhe)(zhe))。30年代后,因(yin)受徽班(ban)和(he)(he)京劇影響,逐漸(jian)移至(zhi)下場的(de)(de)臺側。傳統(tong)的(de)(de)鑼(luo)(luo)鼓(gu)點(dian)(dian)質樸、洗練(lian),常(chang)用的(de)(de)有(you)一(yi)、二、三、四、五、六、九槌,和(he)(he)十三槌半、四不粘(又(you)名(ming)“一(yi)字鑼(luo)(luo)”)、蛤蟆跳缺、鳳點(dian)(dian)頭、三條箭、推公車等。配合身段表演(yan)的(de)(de)有(you)起板鑼(luo)(luo)鼓(gu)、十三槌半、七字鑼(luo)(luo)、叫鑼(luo)(luo)等。建(jian)國(guo)后,又(you)陸續吸收京劇技(ji)藝,編創了(le)一(yi)些新鑼(luo)(luo)點(dian)(dian),以適應表演(yan)和(he)(he)聲腔(qiang)伴奏(zou)的(de)(de)需要。
【黃(huang)梅戲藍橋會討姻(yin)緣抓住我裙邊(bian)所為(wei)哪(na)一件】
黃梅戲藍橋會討姻緣唱詞:
女:肩挑水桶回家轉
男:魏奎元走上前,拉住妹妹裙邊
女:抓住我裙邊所為哪一件
男:我心想與大姐求討姻緣
女:井邊我不把姻緣現
男:我就跪到正二三月清明邊,我也要討姻緣
女:正二三月清明邊,我不把姻緣現
男:我就跪到四五六月大炎天,曬死我這個書呆子我也要討姻
女:六月炎天,我不把姻緣現
男:我就跪到七八九月重陽節,我也要討姻緣
女:九月重陽,我不把姻緣現
男:我就跪到寒冬臘月過年邊,我也要討姻緣
女:臘月二十三,家家要送灶
男:討不到姻緣我不想過年。
【黃梅戲蘭橋討(tao)姻緣肩挑水桶回家轉簡普(pu)請解答】
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